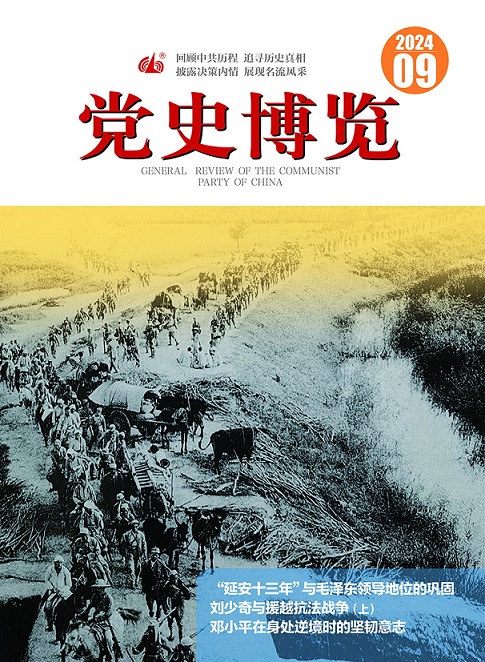<<返回首頁
當前位置: 網(wǎng)站首頁 > 史海鉤沉
從遵義到蘇聯(lián):李德在華后期活動考察
來源:《黨史博覽》2014年第2期 作者:韓洪泉 點擊次數(shù):
■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上,李德受到批評,其軍事領(lǐng)導方式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方針也受到批判,并被寫入會議的總結(jié)決議之中:“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同志指博古,華夫同志指李德)的領(lǐng)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lǐng)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fā)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chuàng)造性是被抹殺了。在轉(zhuǎn)變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zhàn)斗中許多寶貴的經(jīng)驗與教訓完全拋棄,并目之為‘游擊主義’,雖是軍委內(nèi)部大多數(shù)同志曾經(jīng)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jīng)發(fā)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華夫同志與××同志是徒然的。”“政治局擴大會認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chuàng)造新蘇區(qū),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lǐng)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lǐng)導方式。”李德本人參加了遵義會議,伍修權(quán)作為他的翻譯也列席了會議。對于李德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xiàn),伍修權(quán)回憶:“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當時,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我也坐在他旁邊,他完全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上。別人發(fā)言時,我一邊聽一邊翻譯給李德聽,他一邊聽一邊不斷地抽煙,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由于每天會議的時間很長,前半段會我精神還好,發(fā)言的內(nèi)容就翻譯得詳細些,后半段會議時精力不濟了,時間也緊迫,翻譯就簡單些。在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為自己及王明在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不過這時他已經(jīng)理不直、氣不壯了。事后有人說他在會上發(fā)脾氣,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這我沒有見到。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斗爭很激烈,但是發(fā)言還是說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識到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失勢無權(quán)了,只得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發(fā)言。”
李德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國紀事》中是這樣回憶的:“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兩天的會議。伍修權(quán)顯然不樂意給我翻譯,而且譯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會議記錄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決議的文字材料并詳細閱讀之前,沒有表明態(tài)度。”對于會上對他的批評,他認為是“詆毀”,辯解說:“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quán)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lián)系,怎么才能做到這些呢?”同時,他堅持認為遵義會議“不是解決生死攸關(guān)的原則問題,而是一場無原則的派別斗爭”。
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堅持認為自己作為顧問只是提提意見,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而“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黨在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了華夫的名字,而在團以上干部會中才宣布博古的名字。在遵義會議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揮權(quán)。這次會議以后,他參加紅軍領(lǐng)導層決策性會議的次數(shù)逐漸減少,即使應邀參加,也只是列席罷了。
■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義會議結(jié)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紅一軍團去的要求。“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待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diào)的中國內(nèi)戰(zhàn)的特殊性。這一請求被批準了。”于是,“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里領(lǐng)來的特殊供應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趕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后,他終于見到了林彪。他說,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撲克,開始研究毛的戰(zhàn)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fā)過去的”。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早在中央蘇區(qū)時李德還曾去紅一軍團講過戰(zhàn)術(shù)課,當時他與軍團長林彪相處得還算融洽。不過這次前來“蹲點”的李德卻自認為討了無趣:“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tài)度接待了我。關(guān)于軍事形勢,他緘口不談,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事實上,林彪對李德仍很關(guān)照,他特意交代軍團管理科的一名科長負責照顧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紅軍二占遵義城時,李德又回到中央縱隊行動,隨軍轉(zhuǎn)戰(zhàn)貴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長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會議。據(jù)李德回憶,他在會議召開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請,由于沒帶翻譯,只能靠博古邊聽邊給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會上,毛澤東對以林彪為代表的錯誤認識和活動進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態(tài)時卻說:“我們別談過去了,還是談談當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回憶:“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員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林彪、彭德懷也沒有到場。
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8月初,李德被派到紅軍聯(lián)合軍事學校擔任領(lǐng)導。據(jù)他自己回憶:“就戰(zhàn)術(shù)問題上過幾次大課,并且進行過幾次專題的講座和圖上演習,但大部分時間卻是參加‘收割’,甚至有兩次參加了一個征糧隊。”8月3日,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行動。
當時,紅四方面軍領(lǐng)導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堅決抵制分裂,維護黨的決議和統(tǒng)一。他也認為:“我確實也是一個忠實支持者,盡管我對遵義會議持有保留意見。”
對此,時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的閻捷三曾有過回憶:
一天凌晨,紅大師生集合起來準備出發(fā),這時紅軍大學教育長、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帶著人騎馬趕來了。他大聲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四方面軍的同志都隨張國燾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見李特十分囂張,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馬頭,斥責他的分裂言行。沒說幾句話,兩人就動起手來。聞訊而來的毛澤東制止了他們的爭斗。此時,李特情緒非常激動。李德?lián)睦钐匾粫r沖動鋌而走險,就從后面將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氣急敗壞地狂喊亂叫,使勁掙扎,但無奈李德的雙臂如同鋼鐵一般,他怎么也擺脫不掉。毛澤東見狀說了聲:“放了他吧!讓他們走!”見毛澤東發(fā)話,李德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當時在場的彭德懷目睹了這一幕,并說李德“這次表現(xiàn)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
上述一幕,見于2006年8月15日《解放軍報》上發(fā)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揮權(quán)之后》一文。在閻捷三《捉放李特的見聞》中有更為詳細的回憶,彭德懷以及另外幾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也提到了這件事,應當是可信的。李德對自己的這一行動,在《中國紀事》中卻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寫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軍事學校去傳達開拔的命令,我這樣去做了。司令員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來,其間好像沒有發(fā)生沖突,早晨我同學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縱隊。”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關(guān)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將部隊進行了重新編組,李德是編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今吳起縣城)。紅一方面軍勝利結(jié)束長征,李德也成了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繼續(xù)履行顧問職責■
1935年12月,李德隨中央機關(guān)住進瓦窯堡。不久,他參加紅軍參謀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紅軍學校工作。12月27日,他參加了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他對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持反對態(tài)度,認為“它既不符合國內(nèi)實際力量的對比,也無助于建立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民主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目的”。1936年1月,李德列席中央軍委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戰(zhàn)略方針,歸結(jié)起來是如何處理好鞏固和發(fā)展中的關(guān)系。會議決定東征發(fā)展,在發(fā)展中鞏固。李德不同意這個決定,受到其他同志的批評。27日,紅軍主力東征前夕,李德寫信給中共中央,即《對戰(zhàn)略的意見書》,意在說服中央停止東征行動。信中指出:閻錫山有8萬人,在技術(shù)上、交通條件方面都比我們優(yōu)越,我們只有1.3萬人,其中一半是新兵和3000名新的俘虜兵,技術(shù)條件也低。在戰(zhàn)爭形式方面,游擊性的行動在蘇區(qū)和游擊區(qū)常常能決定勝利,但在白區(qū)則很少能得到結(jié)果。同時,李德聲明,“拒絕參加出征的隊伍”。這樣,紅軍主力東征期間,李德在后方留守。其間,白匪民團曾多次襲擾邊區(qū),他還協(xié)助周恩來參加參謀部的工作,并同紅軍軍事學校的全體學員一起參加了保衛(wèi)瓦窯堡安全的戰(zhàn)斗,表現(xiàn)勇敢。5月初,東征回師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李德被邀列席,會上他為阻止東征一事作了自我檢討,承認政治局對他的信的批評“是正確的”。
此后,李德被安排到抗大教學。他還受命負責建立和訓練了紅軍的一個騎兵團。李德憑借在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學過騎兵并當過蘇聯(lián)紅軍騎兵師參謀長的經(jīng)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并認為這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樂趣”。
1937年1月,李德隨中央遷到延安居住。他沒有被邀請參加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他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許多方針政策和軍事策略表示不滿和反對。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為研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zhàn)方法,總結(jié)紅軍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教訓,吸取國外軍事作戰(zhàn)成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軍事研究委員會,李德為委員;在軍事研究委員會下設編委會,李德任主任。1937年9月至10月間,延安的軍事雜志編輯建議李德每月寫一份軍事概況,但李德想按自己的觀點組織文章,結(jié)果文章被拒絕發(fā)表。1938年下半年,他受司令部委托,先后寫了幾篇反映現(xiàn)代武器在不同斗爭中的策略的文章,包括《現(xiàn)代軍事技術(shù)》《坦克及坦克斗爭的方法》《空軍與防空》《化學戰(zhàn)爭與防毒》等。李德回憶說:“這些文章統(tǒng)統(tǒng)發(fā)表了,并署了譯者的名字。只有一次,由于疏忽把李德稱為作者了,我得到了讀者的幾句稱贊,但編輯卻受到了指責。”其中前兩篇文章分別發(fā)表在《八路軍軍政雜志》193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后兩篇文章分別發(fā)表在《中國青年》1939年第四、五期合刊和第八期上。
1938年至1939年間,李德的正式身份是后方司令部顧問。
■爭取返回蘇聯(lián)■
1936年中國共產(chǎn)黨同共產(chǎn)國際恢復無線電聯(lián)系以后,李德曾幾次向洛甫(張聞天)要求返回蘇聯(lián)。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大喜過望,多次找王明和張聞天請求共產(chǎn)國際把他召回蘇聯(lián)。王明則竭力勸阻,說蘇聯(lián)正在搞肅反,李德此時回去很危險。“他的原話是,在蘇聯(lián)等待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須估計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槍殺。他這番話并沒有使我感到十分吃驚,因為在《真理報》上我經(jīng)常讀到我個人認識的或是知道的名字成了‘人民的敵人’,我可以保證,他們對黨的忠誠是堅定不移的。我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和聯(lián)系,但是我對自己說:不管發(fā)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為我自己的工作負責。”在王明的勸說下,李德暫時打消了回蘇聯(lián)的想法,但他還是想在適當?shù)臅r候回蘇聯(lián)。這期間,李德與在延安搞醫(yī)務工作的國際友人馬海德等有較多交往。在此前后,他也曾會晤過到延安采訪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外國人士。埃德加·斯諾訪問陜北期間,也曾同李德長談,李德也對自己在華的軍事指導思想作了反思,承認西方的作戰(zhàn)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tǒng),由中國軍事經(jīng)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zhàn)術(shù)。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zhàn)爭的正確戰(zhàn)術(shù)。”這種認識顯然是較為客觀的。
1939年秋,周恩來赴蘇聯(lián)治病。李德接到中共中央臨時通知,批準他同機返蘇。在延安機場,不少人都趕來同李德告別,毛澤東也禮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這樣,李德結(jié)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李德返回蘇聯(lián)后,受到共產(chǎn)國際的批評,并被禁止再過問中國事務。之后,他去蘇聯(lián)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1941年,李德以紅軍軍官的身份參加了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又回到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國定居,主要從事翻譯工作,是德文版的列寧著作的責任編輯,還翻譯了一些蘇聯(lián)作家的作品。1961年至1963年,李德曾擔任民主德國作家協(xié)會第一書記。
剩下的日子,李德是在平靜中度過的:翻譯,研究,著述。1973年,民主德國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紀事》。在這本書中,李德對當年的一些事實進行了歪曲敘述,并對一些中共領(lǐng)導人進行攻擊、誹謗。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東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