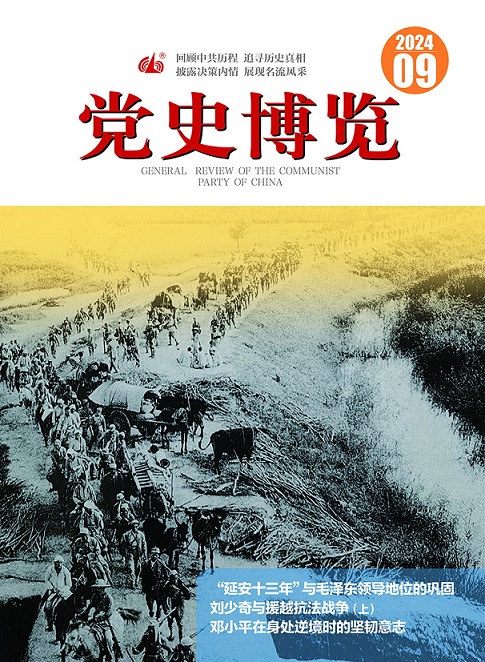當(dāng)前位置: 網(wǎng)站首頁(yè) > 將帥風(fēng)采
劉伯承是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辛亥革命時(shí)期從軍,1926年加入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相繼參加了北伐戰(zhàn)爭(zhēng)、八一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戰(zhàn)爭(zhēng)、長(zhǎng)征、抗日戰(zhàn)爭(zhēng)、解放戰(zhàn)爭(zhēng)等。新中國(guó)成立后,歷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書(shū)記,西南軍政委員會(huì)主席,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事學(xué)院院長(zhǎng)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副主席等職。劉伯承一生指揮了多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屢建奇功。紅軍長(zhǎng)征途中,在后有數(shù)十萬(wàn)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險(xiǎn)的情況下,許多人怕部隊(duì)過(guò)不了江,毛澤東卻風(fēng)趣地說(shuō):“朱德同志說(shuō),四川稱劉伯承是一條龍下凡,江水怎么會(huì)擋得住龍呢?他會(huì)把我們帶過(guò)去的!”劉伯承果然不負(fù)眾望,使大軍安然渡江。晚年,劉伯承身體一直不好,長(zhǎng)期在醫(yī)院住院治療,但他心憂天下,壯心不已,深得全軍上下的尊敬和愛(ài)戴。

1958年5月,中央軍委擴(kuò)大會(huì)議錯(cuò)誤地批判了軍隊(duì)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劉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對(duì)待。1959年9月,他出任中央軍委戰(zhàn)略小組組長(zhǎng)。圖為劉伯承在學(xué)習(xí)馬列主義
■“還是讓我去辦學(xué)校吧!”■
“劉伯承同志有大智大勇,為了中國(guó)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一貫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主動(dòng)承擔(dān)最困難、最危險(xiǎn)的任務(wù),臨危不懼、臨難不茍,赴湯蹈火,義無(wú)反顧。他以無(wú)產(chǎn)階級(jí)軍事家的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和戰(zhàn)略眼光,藐視一切貌似強(qiáng)大的對(duì)手,駕馭戰(zhàn)局的發(fā)展變化,奪取主動(dòng),戰(zhàn)勝?gòu)?qiáng)敵。在幾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身經(jīng)百戰(zhàn),先后負(fù)傷九處之多。”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在為劉伯承致的悼詞中這樣評(píng)價(jià)。
在戎馬生涯中,劉伯承先后負(fù)傷9處,是十大元帥中受傷次數(shù)最多的一位。葉劍英曾詩(shī)贊劉伯承“遍體彈痕余只眼”。陳毅亦詩(shī)稱:“彈觸一目眇,槍傷遍體瘢。”
晚年,劉伯承曾回顧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但從不講戰(zhàn)爭(zhēng)的事,甚至不看戰(zhàn)爭(zhēng)片及戰(zhàn)爭(zhēng)題材的電視劇。一想起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他就有種難言的感覺(jué)。而有件事卻是他津津樂(lè)道的,那就是辦學(xué)。
1949年10月20日,在軍委組成后的第一次會(huì)議上,代總參謀長(zhǎng)聶榮臻就在關(guān)于軍事問(wèn)題的報(bào)告中透露出重要信息:軍委正在籌備陸軍大學(xué)。時(shí)任西南局第二書(shū)記、第二野戰(zhàn)軍司令員的劉伯承,得知消息后給中央寫(xiě)信,提出:“要建設(shè)一支現(xiàn)代化的軍隊(duì),最難的是干部的培養(yǎng)。我愿意辭去在西南擔(dān)任的一切行政長(zhǎng)官的職務(wù),去辦一所軍事學(xué)校。戰(zhàn)爭(zhēng)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我年齡這么大了,還是讓我去辦學(xué)校吧!”
劉伯承早在1927年便赴蘇聯(lián)留學(xué),先后在蘇聯(lián)高級(jí)步兵學(xué)校、伏龍芝軍事學(xué)院學(xué)習(xí),是學(xué)院高才生。回國(guó)后曾任中國(guó)人民抗日軍政大學(xué)副校長(zhǎng),兼任過(guò)中原軍區(qū)、第二野戰(zhàn)軍軍政大學(xué)校長(zhǎng)和政治委員等,有豐富的治校育才經(jīng)驗(yàn)。
經(jīng)過(guò)慎重考慮后,毛澤東同意了劉伯承的請(qǐng)求。
1950年6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陸軍大學(xué)籌備委員會(huì),指定軍委軍訓(xùn)部部長(zhǎng)蕭克為籌委會(huì)主任,當(dāng)時(shí)主要工作是選擇校址。9月,聶榮臻向毛澤東呈送關(guān)于陸大選址問(wèn)題報(bào)告,毛澤東批復(fù):“同意陸大設(shè)在南京。”11月16日晨,周恩來(lái)將《關(guān)于創(chuàng)辦軍事學(xué)院的意見(jiàn)》送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毛澤東對(duì)此表示同意,要求首先要把軍事學(xué)院辦好。
11月21日晚,劉伯承乘火車赴南京,隨即投入緊張的建校和教學(xué)準(zhǔn)備工作。11月30日,軍委任命劉伯承為軍事學(xué)院院長(zhǎng)(1951年2月4日兼任政治委員)。1951年1月15日,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事學(xué)院在南京原國(guó)民黨政府國(guó)防部大院舉行成立典禮。毛澤東親筆題詞:“努力學(xué)習(xí),保衛(wèi)國(guó)防”。同年5月30日,軍事學(xué)院空軍系、海軍系正式成立。至此,軍事學(xué)院成為一所名副其實(shí)的培訓(xùn)陸軍、海軍、空軍中高級(jí)指揮員的綜合性高等軍事學(xué)府。1953年2月22日,毛澤東從安慶乘“洛陽(yáng)”號(hào)軍艦抵南京。次日,毛澤東讓劉伯承和總高級(jí)步校校長(zhǎng)宋時(shí)輪,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別匯報(bào)院校情況。因劉伯承在上海治療眼疾,改由陳伯鈞、鐘期光代為匯報(bào)。毛澤東聽(tīng)了匯報(bào)后,意味深長(zhǎng)地說(shuō):“延安有個(gè)清涼山,南京有個(gè)紫金山。”
建校之初,百?gòu)U待興,特別是缺乏統(tǒng)一適用的教材。毛澤東對(duì)此非常關(guān)心,要求:“軍事學(xué)院把師以上的教材,總高級(jí)步校把團(tuán)以下的教材分別負(fù)責(zé)搞出來(lái),以供給全軍使用。這是一件大事。現(xiàn)在部隊(duì)、學(xué)校普遍就是因?yàn)闆](méi)有教材,感到困難得很。”
劉伯承從上海回到南京,得知這些情況后,立即向全院作了傳達(dá),并召集學(xué)院領(lǐng)導(dǎo)和教授會(huì)同志,研究落實(shí)毛澤東親自交給的編寫(xiě)教材任務(wù)。
在全院大會(huì)上,劉伯承要求各級(jí)干部、教員以及工作人員,以南京比延安,以學(xué)院比“抗大”,以對(duì)黨和軍隊(duì)事業(yè)高度負(fù)責(zé)精神,不圖名利,一輩子忠誠(chéng)黨的教育事業(yè),最后“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從此,“死在南京,埋在紫金山”這句話,就成了軍事學(xué)院干部、教職工的口頭禪,成為他們獻(xiàn)身于黨和軍隊(duì)教育事業(yè)的座右銘。
1955年三四月間,劉伯承趁在北京出席會(huì)議的機(jī)會(huì)向毛澤東反映:由于軍事學(xué)院學(xué)員系不斷擴(kuò)大,學(xué)員人數(shù)不斷增加,教員隊(duì)伍已出現(xiàn)嚴(yán)重缺額。在朝鮮停戰(zhàn)和大軍區(qū)改劃之時(shí),本應(yīng)從全軍選調(diào),但未能如愿。因此,請(qǐng)求批準(zhǔn)從軍事學(xué)院畢業(yè)學(xué)員和其他院校畢業(yè)學(xué)員中選留一批作教員。毛澤東風(fēng)趣地說(shuō):“這個(gè)辦法很好,可是,你怎么不早喊呢?”回到南京,劉伯承立即向毛澤東報(bào)送了《關(guān)于軍事學(xué)院情況及提請(qǐng)補(bǔ)充教員的報(bào)告》,提出:“為了解決學(xué)院教員隊(duì)伍嚴(yán)重缺額的情況,請(qǐng)軍委授予我一個(gè)權(quán)力,不管是從哪里來(lái)的學(xué)員,只要學(xué)有專長(zhǎng),能勝任教學(xué)工作,我都可以選留作教員。”
就這樣,劉伯承胸懷寬廣,不拘一格選人才。
他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訪賢”和“招賢”。不久,10多個(gè)教授會(huì)和翻譯室及俄文訓(xùn)練班成立了。20多位蘇聯(lián)軍事專家請(qǐng)來(lái)了。一批年輕的文化教員也請(qǐng)來(lái)了。
盡管如此,軍事學(xué)院成立之初的教員配備還是比較缺乏。雖然從華東軍政大學(xué)選留了一部分教員,后又從機(jī)關(guān)和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了一定數(shù)量的知識(shí)分子任教員,但仍不能滿足教學(xué)的需要。劉伯承以他獨(dú)有的膽略和氣魄,唯才是舉,從起義投誠(chéng)和解放過(guò)來(lái)的原國(guó)民黨軍官中,先后篩選起用了600多名舊軍官擔(dān)任軍事教員。這些人有的在原國(guó)民黨國(guó)防部任過(guò)職,有的在國(guó)民黨陸軍大學(xué)執(zhí)過(guò)教,有的擔(dān)任過(guò)國(guó)民黨軍隊(duì)的高級(jí)將領(lǐng)。
開(kāi)始,一些學(xué)員對(duì)這些舊軍官出身的教員很不服氣,思想怎么也轉(zhuǎn)不過(guò)彎來(lái),有的干脆說(shuō):“手下敗將來(lái)教打勝仗的,老子不聽(tīng)那一套。”為了做通這些學(xué)員的思想工作,劉伯承語(yǔ)重心長(zhǎng)地說(shuō):“‘舊軍官’是他們的過(guò)去。現(xiàn)在,他們改變了立場(chǎng),為我軍服務(wù),就是我們的老師。”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個(gè)突出例子。一天,劉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請(qǐng)來(lái)講課。劉伯承開(kāi)門(mén)見(jiàn)山地說(shuō):“這次,請(qǐng)你來(lái)當(dāng)我們的老師,主要講三個(gè)方面的問(wèn)題:一是講講你在緬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績(jī)的‘小部隊(duì)?wèi)?zhàn)術(shù)’‘森林作戰(zhàn)法’及‘城鎮(zhèn)村落戰(zhàn)斗’;二是講講你對(duì)遼沈戰(zhàn)役的體會(huì),實(shí)事求是,作戰(zhàn)中,雙方的優(yōu)缺點(diǎn)都可以講;三是講講你對(duì)我軍建設(shè)的建議。”面對(duì)這位名震中外的常勝將軍,廖耀湘有些誠(chéng)惶誠(chéng)恐地說(shuō):“劉院長(zhǎng),我恐怕講不好啊。”劉伯承揮了一下手,說(shuō):“放心講吧,這三方面的問(wèn)題,只有你能講,我們只能當(dāng)你的學(xué)生……”
劉伯承在組建南京軍事學(xué)院時(shí),曾經(jīng)聘請(qǐng)過(guò)一名蘇聯(lián)顧問(wèn)。該顧問(wèn)比較傲慢,經(jīng)常指責(zé)中方學(xué)員不懂軍事。有一次,劉伯承約他談話,談話中用俄語(yǔ)重點(diǎn)闡述了對(duì)俄國(guó)著名軍事家蘇伏洛夫十大軍事原則的理解。該顧問(wèn)聽(tīng)后對(duì)劉伯承的學(xué)識(shí)深感驚訝:“沒(méi)想到中國(guó)還有人對(duì)蘇聯(lián)軍事家研究如此深刻!”從此,他再也不品頭論足了。
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劉伯承留下了390萬(wàn)字的軍事著作和190萬(wàn)字的翻譯作品,令人敬佩。

1959年10月,彭真、羅榮桓、劉伯承、林彪、葉劍英、賀龍(前排左起)等在一起
■“編外參謀”心系前線■
晚年,劉伯承常常憶及的另一件事,就是走邊防。
1958年的“教條主義風(fēng)波”之后,劉伯承生活中籠罩著巨大的陰影,其心理和精神壓力是可以想見(jiàn)的。但是,劉伯承并沒(méi)有消沉。他深信黨的事業(yè)、軍隊(duì)的事業(yè),如同在長(zhǎng)江上航行的船只一樣,不可能完全平直順暢。劉伯承沒(méi)有怨言,沒(méi)有牢騷,泰然處之。他深信黨和人民是公正的。
1959年1月19日,67歲的劉伯承攜家眷由南京回到北京。9月,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戰(zhàn)略小組組長(zhǎng),副組長(zhǎng)是徐向前。在一般人眼里,戰(zhàn)略小組組長(zhǎng)算是個(gè)虛職,可劉伯承不這樣認(rèn)為,他夙興夜寐地為國(guó)防建設(shè)特別是戰(zhàn)備工作操勞。
劉伯承撐著殘弱的病體,深入部隊(duì),深入邊防,調(diào)查研究,了解情況,實(shí)事求是地分析問(wèn)題,親自動(dòng)手給中央軍委寫(xiě)出詳細(xì)的考察報(bào)告。從世界戰(zhàn)略形勢(shì)到未來(lái)反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場(chǎng)準(zhǔn)備,從一種武器的研制、一條鐵路線的修筑,到每個(gè)戰(zhàn)士負(fù)荷的減輕,他無(wú)不精心擘畫(huà)和周密思考,并及時(shí)向中央軍委和總參、總政、總后提出建議。
他常常說(shuō),自己是一名“傷殘軍人”,是軍委的“編外參謀”,所提建議僅供軍委和各總部決策時(shí)參考。他一再反對(duì)人們把他的話當(dāng)作什么批示,但是,實(shí)際上,他的諸多深思熟慮、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的建議,總是受到軍委和各總部的重視,在加強(qiáng)國(guó)防建設(shè)和保衛(wèi)邊疆的斗爭(zhēng)中起到重要作用。
■ 在對(duì)印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中當(dāng)“參謀” ■
1962年6月,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越過(guò)“麥克馬洪線”,入侵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區(qū);在西段的中國(guó)領(lǐng)土上,非法設(shè)立了侵略據(jù)點(diǎn)。10月20日,印軍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同時(shí)向中國(guó)邊防部隊(duì)發(fā)動(dòng)了大規(guī)模的武裝進(jìn)犯。
這天,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同時(shí)展開(kāi)。在東段,實(shí)施主要突擊的右翼部隊(duì)迅速攻克了槍等、卡龍、扯冬等地;左翼助攻部隊(duì)密切配合,相繼攻下沙則、仲昆橋,同時(shí)迂回到章多。至當(dāng)天下午,印軍大部被殲,一部潰逃。后來(lái),我邊防部隊(duì)又分兵5路,乘勝追擊,直取達(dá)旺。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duì)向加勒萬(wàn)河谷、紅山頭的入侵印軍實(shí)施反擊。激戰(zhàn)1小時(shí),全殲入侵之?dāng)常M(jìn)而乘勝擴(kuò)大戰(zhàn)果,掃除了班公湖兩岸及其以北地區(qū)的印軍侵略據(jù)點(diǎn)。
劉伯承在北京看到第一階段作戰(zhàn)的捷報(bào)之后,十分高興。他估計(jì)印軍不會(huì)善罷甘休,而我們的反侵略作戰(zhàn)還可能繼續(xù)打下去。
他打電話給總參,詢問(wèn)參戰(zhàn)部隊(duì)的休整情況,分析印軍的動(dòng)向,印軍反撲可能使用的兵力,了解戰(zhàn)區(qū)的交通狀況,哪些河流能通航等等。
劉伯承要求總參告訴前線部隊(duì):“通向前面的道路要急速加修。立即組織專人調(diào)查所控制地區(qū)內(nèi)的地形、道路和居民點(diǎn)情況,部隊(duì)到哪里,哪里的這些情況就要搞清楚、弄準(zhǔn)確,重要地理問(wèn)題不能忽視。這一點(diǎn)搞不好,就等于失去了作戰(zhàn)指揮。”重視地形和道路問(wèn)題,主要是為了保障運(yùn)輸暢通和后勤補(bǔ)給及時(shí)。因此,他再次關(guān)切地指出:“印軍后縮,運(yùn)輸條件比以前好了,而我們運(yùn)輸補(bǔ)給要困難些,印軍可能用空軍封鎖我們,應(yīng)預(yù)先作好防護(hù)準(zhǔn)備。”
11月中旬,印軍果然調(diào)集了更多的兵力、武器,準(zhǔn)備繼續(xù)向中國(guó)軍隊(duì)進(jìn)攻,并置重點(diǎn)于中印邊境東段。為了遏制中國(guó)軍隊(duì)的正面反攻,他們?cè)谖鞑厣侥系貐^(qū)的西山口一帶作了前重后輕的分段部署,形成了外線較強(qiáng)、側(cè)后較弱的配置。這個(gè)特點(diǎn)一下子被劉伯承抓住,他指出:“目前敵人的配置,東段敵人兵力重點(diǎn)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上,其特點(diǎn)是:銅頭、錫尾、背緊、腹松……從西北向東南擺成一字長(zhǎng)蛇陣對(duì)我組織防御。在西山口方向,敵人左翼就是它的肚子,從這里開(kāi)它,要比砍背容易些。”他要求部隊(duì)采取迂回包圍的戰(zhàn)法應(yīng)對(duì),并說(shuō):“分進(jìn)合擊是軍事原則,是一個(gè)重要的戰(zhàn)法。正面攻擊和迂回的部隊(duì),遠(yuǎn)距離迂回和近距離包圍迂回的部隊(duì),這個(gè)方向和那個(gè)方向的部隊(duì),步兵和炮兵等等,都要切實(shí)協(xié)調(diào)一致動(dòng)作。”在指揮上,他特別關(guān)照部隊(duì)指揮員:“一是道路須順暢,要作專門(mén)調(diào)查,抓好這一點(diǎn)就抓住了關(guān)鍵;二是要統(tǒng)一時(shí)間、計(jì)劃,還應(yīng)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確保其實(shí)施,對(duì)影響部隊(duì)開(kāi)進(jìn)和運(yùn)動(dòng)的各種因素,事先都要作好仔細(xì)的考慮;三是各方向的部隊(duì)要有獨(dú)立作戰(zhàn)能力。這幾點(diǎn)搞好了,分進(jìn)合擊就有把握。”
身在北京,心在前線,劉伯承幾乎把作戰(zhàn)部隊(duì)可能遇到的問(wèn)題都想到了,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實(shí)可行的對(duì)策。可謂運(yùn)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11月14日至16日,印軍再次發(fā)動(dòng)進(jìn)攻。
16日,中國(guó)邊防部隊(duì)堅(jiān)決還擊,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第二階段的戰(zhàn)斗打響。在東段西山口方向,根據(jù)劉伯承“打頭、擊背、剖腹、切尾”的指示,西藏邊防部隊(duì)采取鉗制正面,夾擊兩翼和迂回腹背的戰(zhàn)術(shù),一舉形成對(duì)入侵印軍的合擊態(tài)勢(shì)。18日發(fā)起總攻,先后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馬東、德讓宗、邦迪拉等地;同日晚,在東段的另一方向瓦弄地區(qū),我邊防部隊(duì)主力直插印軍縱深,全部拔除設(shè)立在實(shí)際控制線中國(guó)一側(cè)的侵略據(jù)點(diǎn)。21日,我邊防部隊(duì)逼近了中印傳統(tǒng)習(xí)慣邊界線。山南、林芝邊防分隊(duì)順勢(shì)進(jìn)攻,很快到達(dá)了預(yù)定地區(qū)。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duì),拔除了班公湖地區(qū)入侵印軍殘存的6個(gè)侵略據(jù)點(diǎn),并將印軍趕回到傳統(tǒng)習(xí)慣邊界線印方一側(cè)。
11月21日,中國(guó)政府發(fā)表聲明,宣布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邊防部隊(duì)在中印邊境全線停火,并自12月1日開(kāi)始主動(dòng)回撤至中印雙方實(shí)際控制線中國(guó)一側(cè)。中國(guó)邊防部隊(duì)還奉命將作戰(zhàn)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及其他軍用物資,交還給印度,并釋放被俘人員。
■ 考察日本關(guān)東軍地下工事群,尋找蘇日之戰(zhàn)背后的戰(zhàn)場(chǎng)秘密 ■
對(duì)印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劉伯承不顧年老多病,又帶人前往東北邊防勘察。
1964年7月4日,劉伯承帶領(lǐng)幾名參謀人員先到沈陽(yáng),然后經(jīng)吉林省延邊朝鮮自治州北上,到達(dá)牡丹江市,接見(jiàn)了黑龍江省委和公安縱隊(duì)負(fù)責(zé)人,乘船巡視了鏡泊湖周圍的地形,參觀了一個(gè)軍工廠。

1964年7月24日,劉伯承(前左一)在海拉爾市察看當(dāng)年日本關(guān)東軍修筑的地下工事群
7月16日,劉伯承由嫩江赴哈爾濱。在哈爾濱,他聽(tīng)取了黑龍江省軍區(qū)負(fù)責(zé)人的工作匯報(bào),詳細(xì)觀看了省軍區(qū)的農(nóng)、林、漁場(chǎng)分布形勢(shì)圖。
回到住地,劉伯承結(jié)合邊防情況進(jìn)行了分析,然后向隨行參謀提出:“你們研究一下,若是像新疆那樣在這里也組建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tuán),按照黑龍江邊境地區(qū)現(xiàn)有農(nóng)場(chǎng)數(shù)目,在實(shí)際需要上夠不夠,哪些地區(qū)是戰(zhàn)略要點(diǎn),如何建設(shè)生產(chǎn)兵團(tuán),讓沈陽(yáng)軍區(qū)考慮請(qǐng)他們最近提出意見(jiàn)來(lái)。”
20日,劉伯承繼續(xù)北上,途經(jīng)齊齊哈爾市,視察了兩個(gè)軍工廠。在觀看試制的火炮、炮彈圖樣和實(shí)物樣品時(shí),他說(shuō):現(xiàn)代戰(zhàn)爭(zhēng)機(jī)動(dòng)性很重要,我們既要生產(chǎn)大口徑的火炮,同時(shí)也要研究和生產(chǎn)輕便的、便于機(jī)動(dòng)的、多種用途的火炮和炮彈,適用于山地、叢林作戰(zhàn),拆卸靈便,能打空中飛機(jī)、海上的輕型艦艇、陸地上的坦克和碉堡。
幾天后,劉伯承到達(dá)了他東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海拉爾市。在市郊北山,他認(rèn)真察看了當(dāng)年日本關(guān)東軍修筑的地下工事群。他先是結(jié)合周圍地形,詳細(xì)研究了工事外部的結(jié)構(gòu)和體系,然后下到工事里邊,對(duì)其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包括進(jìn)出口通道、射界范圍、離地高度、抗擊能力,以及容量、厚度、生活衛(wèi)生設(shè)施等,都一一作了細(xì)致的觀察。由于天氣酷熱,坑道內(nèi)潮濕、霉?fàn)€、臭味撲鼻,加之整整一個(gè)上午沒(méi)有休息,鉆出工事時(shí),隨行人員都汗流浹背,疲憊不堪,可他卻始終興致盎然。一出工事,他就對(duì)海拉爾軍分區(qū)負(fù)責(zé)人說(shuō):
“聽(tīng)說(shuō)蘇軍在這里進(jìn)攻時(shí),日本人死了不少,許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蘇軍是怎樣打下來(lái)的,日軍是怎樣被殲滅的?聽(tīng)說(shuō)蘇軍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決問(wèn)題的,把實(shí)際情況弄清楚,調(diào)查研究后向軍委寫(xiě)個(gè)報(bào)告。”
他還對(duì)隨行的參謀說(shuō):“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軍隊(duì)當(dāng)時(shí)總體布局。日本在滿洲里、海拉爾這個(gè)方向上,可能是個(gè)師團(tuán),以滿洲里為前線陣地,布置有一個(gè)大隊(duì)或者一個(gè)聯(lián)隊(duì),海拉爾附近地域內(nèi)基本陣地,布置有一個(gè)聯(lián)隊(duì),預(yù)備隊(duì)為一個(gè)聯(lián)隊(duì)。在海拉爾北山構(gòu)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結(jié)合的碉堡工事,東面可能是彈藥庫(kù),西面是指揮部,方向?qū)χ鴿M洲里,這樣的部署,可以研究參考。”
29日,劉伯承返回哈爾濱。在25天的行程中,劉伯承和當(dāng)?shù)攸h、政、軍的領(lǐng)導(dǎo)干部進(jìn)行磋商,就邊防建設(shè)、戰(zhàn)備工作、軍事訓(xùn)練、武器制造、工事構(gòu)筑等問(wèn)題提出了切合實(shí)際的非常明確的意見(jiàn),為中共中央軍委、總部制定戰(zhàn)略計(jì)劃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不幸的是,在結(jié)束這次視察活動(dòng)后,他的眼疾加重,眼壓又高達(dá)70多度,最后被確診為青光眼急性發(fā)作,不得不專車返京,住進(jìn)醫(yī)院治療。
■從下雪考慮到國(guó)防和人民生活■
晚年,劉伯承病魔纏身,備受折磨。這一切,自然為他的許許多多的老戰(zhàn)友、老部下所牽掛。
1965年春節(jié),原八路軍129師的幾位參謀——王樂(lè)天、李炳輝、王南、衛(wèi)壘、廖開(kāi)芬和機(jī)要秘書(shū)廖家眠等,在鐘澤民的邀集下,到劉伯承家拜年。兩間房大小的客廳,擺著兩套帶補(bǔ)丁的淺藍(lán)色布套的舊沙發(fā)和幾把椅子,房角放著一臺(tái)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jī)。客人們等在客廳里,劉伯承被一名戰(zhàn)士攙扶著走出來(lái)。他的視力衰退更嚴(yán)重了,大家心里不禁為之一怔,發(fā)出“廉頗老矣”的感嘆!
汪榮華好像寬慰大家似的笑著說(shuō):“斗大的字還可以認(rèn)出來(lái),衣服的顏色還可以分辨。”
劉伯承元帥還是那么樸素、熱情、平易近人。他戴一頂舊毛線帽,身穿一套舊棉軍衣,面容清癯,但精神很好。他非常興奮、愉快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認(rèn)真聆聽(tīng)每一個(gè)人的聲音,還能清楚地記得他們的名字,指出誰(shuí)是哪一個(gè)科的參謀,當(dāng)時(shí)的科長(zhǎng)是誰(shuí)。
當(dāng)時(shí),鐘澤民帶上了在北海艦隊(duì)當(dāng)航空兵回北京探視的大兒子,劉伯承拍著他的肩頭,分外感慨地說(shuō):“當(dāng)時(shí)你們參加革命時(shí),也才十幾歲,也是這么高的青年。現(xiàn)在,你們的娃娃都這么大了,我們?cè)趺茨懿焕习。 彼尫蛉送魳s華趕快把別人送給他的浙江溫州蜜橘弄一大盤(pán)來(lái)招待大家。
在與大家閑談中,話題轉(zhuǎn)到最近下的幾場(chǎng)大雪,他轉(zhuǎn)過(guò)身來(lái)問(wèn)鐘澤民:“你是從四川來(lái)的,這幾場(chǎng)大雪下得好,瑞雪兆豐年嘛!但西藏同四川不同,那里是大雪山,交通困難。那里的人民是拾牛糞當(dāng)柴燒的,這樣大的雪,拾牛糞就困難了。你是否知道西藏近幾年搞出煤了沒(méi)有?萬(wàn)一國(guó)家有事,軍隊(duì)要保衛(wèi)邊防,是不能只靠牛糞燒飯的,沒(méi)有煤炭怎么行?”
鐘澤民不大了解這方面的情況,考慮一下說(shuō):“胥光義同志過(guò)去負(fù)責(zé)過(guò)進(jìn)藏支前工作,現(xiàn)在在地質(zhì)部工作,可能了解這個(gè)問(wèn)題,我回去后立即向他轉(zhuǎn)達(dá)。”劉伯承滿意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
看到老元帥能從下雪考慮到國(guó)防和人民生活兩件大事,在場(chǎng)的人既深受教育,又感慨不已。然而,此時(shí)備受病痛折磨的劉伯承,還遭遇著已經(jīng)降臨的政治風(fēng)暴的無(wú)情摧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戰(zhàn)略小組辦公室被撤銷,戰(zhàn)略小組也徒有虛名。
從此,劉伯承不再有實(shí)質(zhì)性的工作可做,完全處于賦閑狀態(tài)。但是,他依然把國(guó)防建設(shè),部隊(duì)的戰(zhàn)備訓(xùn)練,把黨和國(guó)家的前途命運(yùn)掛在心上。他以殘弱多病的身體,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協(xié)助和支持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的工作,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安慰逆境中的聶榮臻■
1966年秋,劉伯承不堪忍受城里住所周圍造反聲浪的干擾,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葉劍英和聶榮臻也搬到這里。陳毅、徐向前經(jīng)常來(lái)看他們。于是,5位元帥在西山時(shí)有會(huì)晤,一起談?wù)摗拔幕蟾锩钡男蝿?shì),商討保持軍隊(duì)穩(wěn)定的辦法。
這年12月12日,傳來(lái)了吳玉章逝世的消息。劉伯承聽(tīng)后萬(wàn)分悲痛。吳玉章是老同盟會(huì)員,也是劉伯承參加革命的引路人,兩人是師生加戰(zhàn)友的雙重關(guān)系。吳玉章的去世,對(duì)體弱多病的劉伯承又是沉重的一擊。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張春橋、姚文元的陰謀策劃與指揮下,篡奪了上海市黨政大權(quán)。一時(shí)間,“一月革命”引發(fā)的奪權(quán)風(fēng)暴在全國(guó)各地驟然刮起。
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葉劍英、陳毅、聶榮臻和劉伯承又聚在一起談到深夜。他們一致認(rèn)為:軍隊(duì)決不能被奪權(quán)。軍隊(duì)必須保持穩(wěn)定。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已是刻不容緩。在非常時(shí)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須搞出幾條命令才行。應(yīng)明確規(guī)定不能沖擊軍事機(jī)關(guān),不準(zhǔn)隨意揪斗各級(jí)領(lǐng)導(dǎo)干部,不準(zhǔn)成立所謂的戰(zhàn)斗組織等。
2月中旬,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李先念等人,由于對(duì)“文化大革命”許多錯(cuò)誤做法強(qiáng)烈不滿,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kāi)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huì)上,與江青等人發(fā)生了激烈的沖突。江青等蓄意歪曲事實(shí)真相,顛倒黑白,將陳毅、葉劍英、徐向前等人的抗?fàn)幷_蔑為“二月逆流”,隨即發(fā)動(dòng)了一連串的批斗與圍攻。
不久,聶榮臻病倒了,住進(jìn)了301醫(yī)院。正在301醫(yī)院治眼疾的劉伯承聞?dòng)崳活欁笱垡呀鳎髦鴣?lái)到聶榮臻的病房。他緊緊地握住聶榮臻的手,千言萬(wàn)語(yǔ)不知從何說(shuō)起。
劉伯承和聶榮臻同是四川人,早年同在上海,后轉(zhuǎn)到中央蘇區(qū),又共同參加長(zhǎng)征。在長(zhǎng)期的革命生涯中,兩人情同手足。想到這些,劉伯承不禁感慨萬(wàn)千。良久,他才說(shuō)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
這在平常情況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話,可在那種險(xiǎn)惡的政治環(huán)境下,它的意義和力量卻顯得那么不平常。
事過(guò)多年,聶榮臻回憶這一情景時(shí)還滿懷感激地說(shuō):“當(dāng)時(shí)我身處逆境,老戰(zhàn)友的這種安慰是多么珍貴啊!”
■一封長(zhǎng)信■
不久,由于眼疾加重,經(jīng)周恩來(lái)批準(zhǔn),劉伯承離開(kāi)了政治熱浪襲人的北京,前往濟(jì)南治療。
后來(lái)濟(jì)南社會(huì)秩序混亂,住地很不安寧,劉伯承又先后轉(zhuǎn)赴南京、上海治療。治療期間,劉伯承常常對(duì)前來(lái)看望的部隊(duì)領(lǐng)導(dǎo)干部說(shuō),軍隊(duì)一定要保持穩(wěn)定,一定要防止過(guò)火行動(dòng),內(nèi)部要團(tuán)結(jié),不要出亂子。他還用歷史上內(nèi)憂外患的事例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內(nèi)憂與外患總是聯(lián)系著的,沒(méi)有內(nèi)憂,必?zé)o外患;如有內(nèi)憂,終有外患。最要緊的是內(nèi)部要團(tuán)結(jié)一致,時(shí)刻警惕敵人鉆空子,在混亂中搞垮我們。
1969年10月18日,劉伯承被通知疏散到武漢。10月20日,他處理了文件資料后始去武漢,后又轉(zhuǎn)赴上海。在上海,他繼續(xù)治療視力極其微弱的左眼。
1970年5月,劉伯承創(chuàng)建的南京軍事學(xué)院、北京高等軍事學(xué)院與政治學(xué)院、后勤學(xué)院合并,成立中國(guó)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xué),校址設(shè)在高等軍事學(xué)院。
得知這個(gè)消息后,劉伯承決定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冊(cè)軍事理論圖書(shū),送給軍政大學(xué)圖書(shū)館。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劉伯承對(duì)前去探望他的軍政大學(xué)校長(zhǎng)蕭克說(shuō):“我現(xiàn)在年紀(jì)大了,眼睛也不行了。這些教材和圖書(shū)留給你們,希望你們把學(xué)校辦好!”
“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撤銷了由林彪死黨黃永勝等人把持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huì)議,負(fù)責(zé)軍委日常工作。
1972年2月,劉伯承給葉劍英寫(xiě)了一封長(zhǎng)信,信中說(shuō):“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我的身體漸趨不好。但是,從關(guān)心黨的事業(yè),關(guān)心軍隊(duì)建設(shè)出發(fā),凡是他們?cè)敢鈫?wèn)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問(wèn)題,我都以參謀的身份向他們提出來(lái)。當(dāng)然,我的那些意見(jiàn),都是些老經(jīng)驗(yàn)、老生常談的東西,不一定適合新的情況,而他們基本上是聽(tīng)了算了,很少回過(guò)話。現(xiàn)在我是個(gè)老弱病殘的人了,又總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對(duì)這次軍委擴(kuò)大會(huì)議,也想盡一份力量。但是,力不從心,難能給你們當(dāng)個(gè)參謀了……為了給會(huì)議研究問(wèn)題提供點(diǎn)資料素材,我請(qǐng)作戰(zhàn)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來(lái)說(shuō)過(guò)的一些話(限于精力和時(shí)間未加校對(duì)),把那些‘古董貨’翻出來(lái),作為一孔之見(jiàn),即送你們一份,供研究參考。”
劉伯承呈送給中共中央軍委的材料,包括他對(duì)軍事訓(xùn)練、院校建設(shè)、參謀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對(duì)海空邊防建設(shè)、國(guó)防戰(zhàn)備工事構(gòu)筑,對(duì)未來(lái)反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方針和作戰(zhàn)指導(dǎo)等一系列問(wèn)題的看法和建議。這些深謀遠(yuǎn)慮的戰(zhàn)略判斷和經(jīng)驗(yàn)之談,是劉伯承幾十年軍事生涯的結(jié)晶,也是他向黨、向人民所作出的最后一次奉獻(xiàn)。
葉劍英指示總參謀部,將劉伯承自1960年以來(lái)的講話匯集起來(lái),印發(fā)軍委各總部、北京軍區(qū)及各有關(guān)部門(mén)參照?qǐng)?zhí)行。
1972年,劉伯承的左眼也失明了,健康狀況更趨惡化,不得不住院進(jìn)行長(zhǎng)期治療。中央對(duì)劉伯承的身體狀況十分關(guān)心,周恩來(lái)曾3次親臨醫(yī)院探視,醫(yī)護(hù)人員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效果仍然不明顯。
毛澤東得知后親自過(guò)問(wèn),周恩來(lái)迅速作出“劉帥的病要以養(yǎng)為主”的指示。然而,由于劉伯承年事已高,殘弱多病的身體終不能復(fù)原而長(zhǎng)期臥床不起。
劉伯承逝世的時(shí)候,鄧小平率全家最先來(lái)到劉伯承的靈堂,向劉伯承深深地三鞠躬,親自主持了追悼會(huì);胡耀邦致悼詞。鄧小平撰寫(xiě)《悼伯承》一文,在《人民日?qǐng)?bào)》上發(fā)表。在文中,鄧小平深情地說(shuō):“伯承久病,終于不治。我和他長(zhǎng)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辭世,使我至為悲痛。”■